我记得那一次和女儿的聊天。我的女儿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住校的。我也从来不接送她。那一次,她读完了初三第一学期。放寒假的那一天,学校召开了家长会。我让她坐上我回家的顺风车。车上,我对她说:“今天,家长会上,你们校长批评了你们初三的学生,说了你们很多的不是——看小说,玩手机,打瞌睡,抄作业,谈恋爱......”
-

-

在我发布的文章《詹大年/摁住学生强行剪头发,被教坏的是谁?谁来背锅?》收到了127条留言。所有的留言,只要不是说脏话的,我都会放出来——不是同意你的观点,仅仅是表示对关注与留言的一种尊重。
-

去年,丑小鸭中学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去爬山,我看到孩子们狂野的样子,随手拍了几张照片发在朋友圈里。有位网友马上给我留言了:“詹校,你们就这么任由学生玩吗?”我说:“是呀。”网友回复:“这样毫无目的的爬山也太浪费时间了嘛。” 我说:“那要怎样才算不浪费时间?”
-

2024年1月28日凌晨3点多,我梦中得到灵感,将“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数学课”简称为“国数课”,从而解决了我撰写《祖国需要,我就去教》一文中重复这一长词组的问题。白天想到的“大数学课”“数思课”“道数课”……我都不满意。将“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数学课”凝练成了一颗种子,起初只是为行文方便,后来这粒种子不断长大,从我的课堂,长到了更多老师的课堂里。正如大作家王蒙先生所言:“简约明快的命名,提升着人的精神,涵育着人的心灵,鼓舞着人的自信,推动着人的奋进。
-

放寒假了,大家都在关注学生的假期安全问题。政府关注,社会关注,学校关注。说白了,学生的假期安全关系千家万户,也关系到关注者的自身利益。 各种“一封信”,都在提醒家长,告诫孩子。凡是想到了的,都必须交代清楚:防冻,防滑,防溺水,防传染病,防暴饮暴食,防烟花炸伤,防压岁钱被骗,防乱花钱,防车祸,防单车撞人,防踩踏事故,防感冒,防吃错药,防触电,防沉迷电游,防不良信息,防信谣传谣,防贪吃贪睡,防暴恐,防电诈,防陌生人......防肚子拉稀,防成绩下滑,防被同学弯道超车......
-

早几天,我的一篇文章,《詹大年/摁住学生强行剪头发,被教坏的是谁?谁来背锅?》挺火热的。有一些留言(估计是同行写的)让我真的不想回复,也找不到回复的词儿。其实,每次我写的站在学生立场的热点文章背后都有批评的、指责的甚至谩骂的留言,但我已经习惯了——既然写不同观点的文章,就首先要做好挨骂的心理准备。越是这样,我觉得我的文章越有意义。很多时候确实非常无奈,也非常无力,我只有在内心为孩子们祈祷——“孩子啊,千万不要落到他们手里!”
-

放假了,一些家长看到孩子玩手机,就焦虑了,崩溃了。 那么,我们应该问自己:孩子如果不玩手机,玩什么?还有什么比手机更好玩的? 关键词:玩。玩什么。
-
詹大年/陈行甲前天刚说“不领薪水”,俞敏洪今天就宣布“150万年薪”聘请陈行甲

这也是一次个人选择、机构转型与社会趋势的三重交汇。 陈行甲的转身,或许正勾勒出一种新的可能性:公益人可以成为商业与社会价值之间的“翻译者”与“催化剂”,而企业也能通过吸纳公益智慧,走向更有温度、更具韧性的发展路径。
-

看见自己的内在,每一种情绪都是童年没被满足的需要。以小孩为镜子照见自己,关键是看自己。儿童教育,关键是自信心。有了自信就会自主,有了自主才有创造。不需要培养,他原本就是自信的,只需呵护和维护就行。但你要知道自信最重要,围绕自信心建构你和孩子的关系和交往。自信是天性,让孩子活在自信里就是活在天性里,他就有勇气和智慧。自信带来自主,自主带来创造。
-

我去过一所“薄弱学校”,这是一所600来个孩子的公办初中,近一半在学校寄宿。我发现,这所学校的学生用不到热水——一年四季都是这样。我问原因。学校领导回答:“水是有的,也安装了4台空气能热水器,但无法运行。因为学校交不起热水器的电费。”
-

当我喝下一口水的时候,突然发现,我喝下的不止是水,还有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品德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,还有哲学、逻辑学、心理学、美学,还有音乐,也可能还有体育。
-
詹大年/最简单的评价是考试,最粗暴的“教育”是刷题……取消统考后的教育怎么做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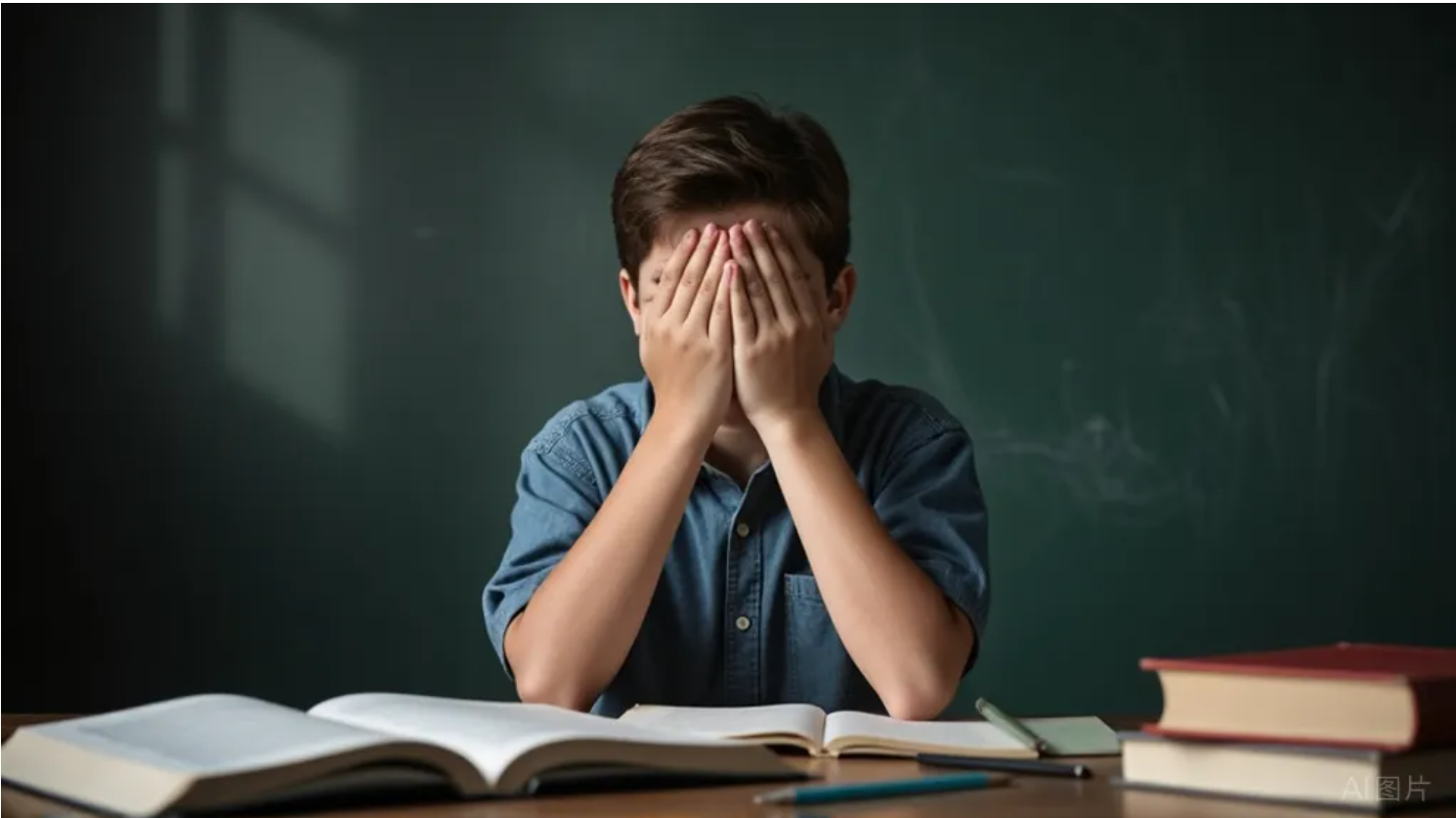
取消期末统一考试后,学校“教育”可能会穿帮了。因为,最简单的评价是考试,最粗暴的”教育”是刷题。不放辣椒,很多的湖南厨师不会炒菜,不搞考试,我估计很多的老师不会教书了。统考取消后,几个问题需要思考:第一个问题,家长会不会更焦虑?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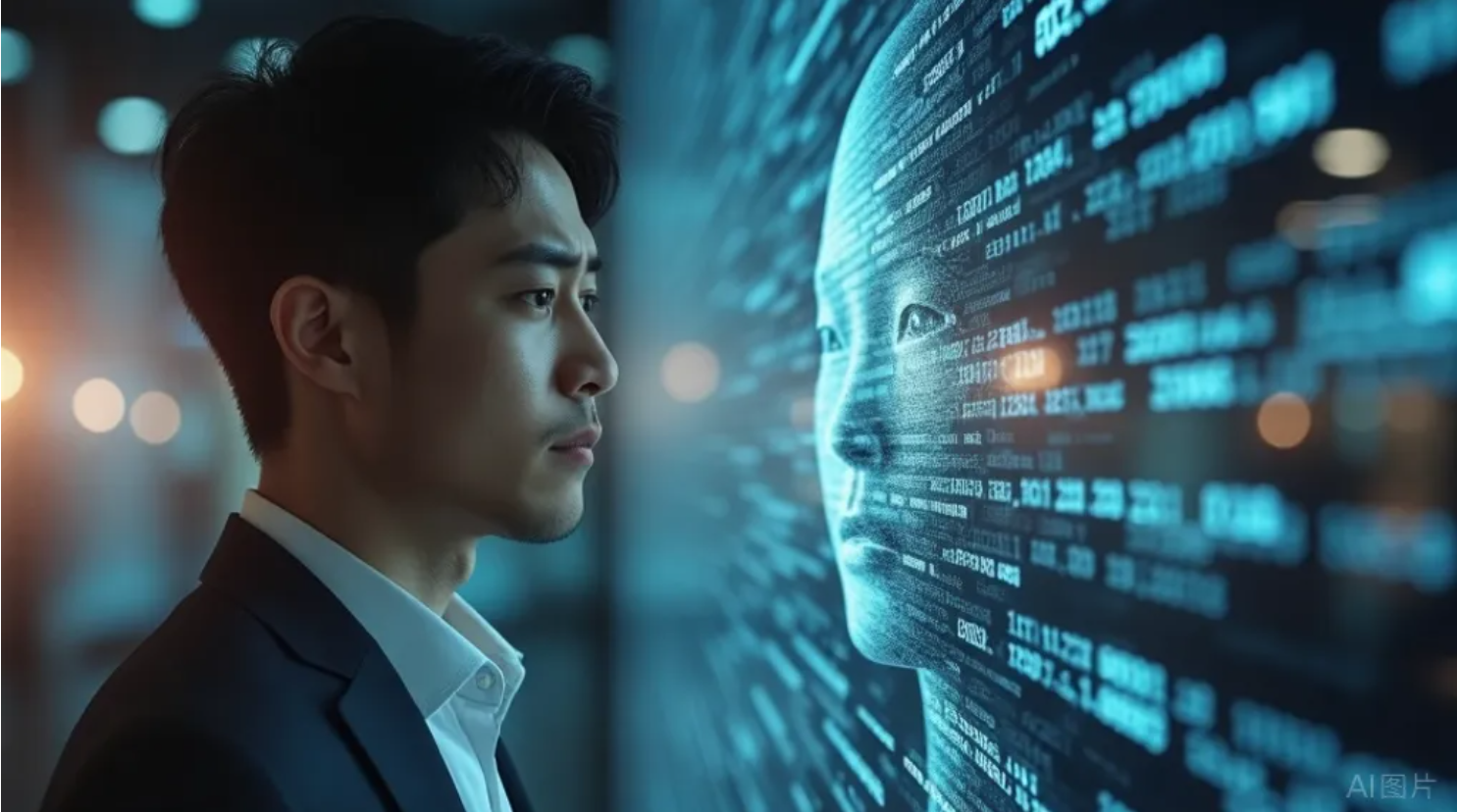
我分别给豆包、DeepSeek、元宝发送国相同在指令——请用1500字左右,评价一下微信公众号“詹大年私号”。AI时代,人类的逻辑判断能力、社会建构能力十分重要。否则,以前被别人骗,以后被AI骗。读书很重要,更重要的是读有思想的书,讲逻辑的书,有人性的书,通向幸福之路的书。
-
詹大年/“我不想醒过来了......”12岁女孩的遗言,可以当教材

——12岁的女孩留下这段话,吞下了大把的治疗心脏病的药,就这么走了。孩子留下的那一段话,是那些曾经被折磨或者正在被折磨的孩子们的心声。这一段话,堪称教科书,给我们成年人以警示。
-

宋记者:我想采访一下,之前你多有责备老师甚至批评老师,现在怎么转变为爱老师了呢?李炳亭:爱之深,责之切,因为责备批评不管用。从根本上说,教育问题的责任不在教师,教师也是受害者,教师不幸福是才是问题的根源。
-

“教育并非只有强制和纵容两种方式。”——这是网友西楼残月的留言。在我发布《詹大年/摁住学生强行剪头发,被教坏的是谁?谁来背锅?》之后,留言很多,也很激烈,而这一则留言简单而富有哲理。说实在的,一些留言,真的不值得去回复——我从来就会把所有的留言放出来,但有的留言真的不值得去回复。因为,这样的人应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读书了。他们只是声称做教育,其实根本就不爱孩子。
-

“有偿补课”是一条产业链,家长和孩子在产业链的最末端。在这条产业链里,除了处在末端的家长和孩子,没有谁不是获利者。但是,天下毕竟只有两种人——一种人叫家长,一种人叫孩子。那么,谁又不是家长,谁又不是孩子呢?
-

在校门口摁住学生强行剪头发的行为是恶劣的。这样的情形确实少见,但规定学生发型的学校很多,不达标不准学生进校园的情形也并不少见,有些学生甚至因此而失学。关于学生“发型”的文章,我写过不少。以下,是我对这一事件的思考
-

“升学率”的本质是利益:是官员的政绩,是学区房的利润,是房贷的利息,是教师的职称,是某些人的灰色收入……你能“反对”? “升学率”的背后是家长半辈子的心血,也是孩子(几乎是所有孩子)青春的全部赌注……“片面追求升学率”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丧失。你能不把“反对”的声音喊大一点?
-

谈及学生管理,不少家校常会因学生厌学叛逆、行为失范等问题束手无策,甚至满心无奈。其实,无论企业管理还是教育管理,皆有其内在的艺术与规律。除了刚性的制度约束,柔性的人文关怀更是不可或缺的内核,这一点在教育管理中尤为凸显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