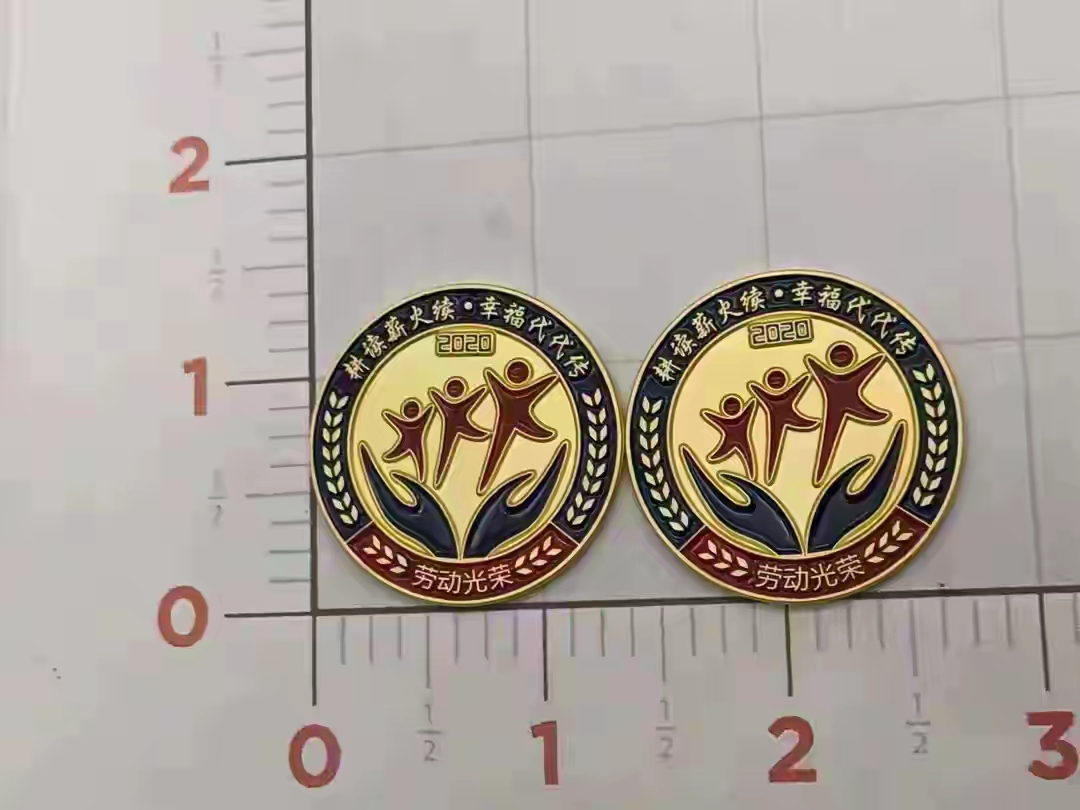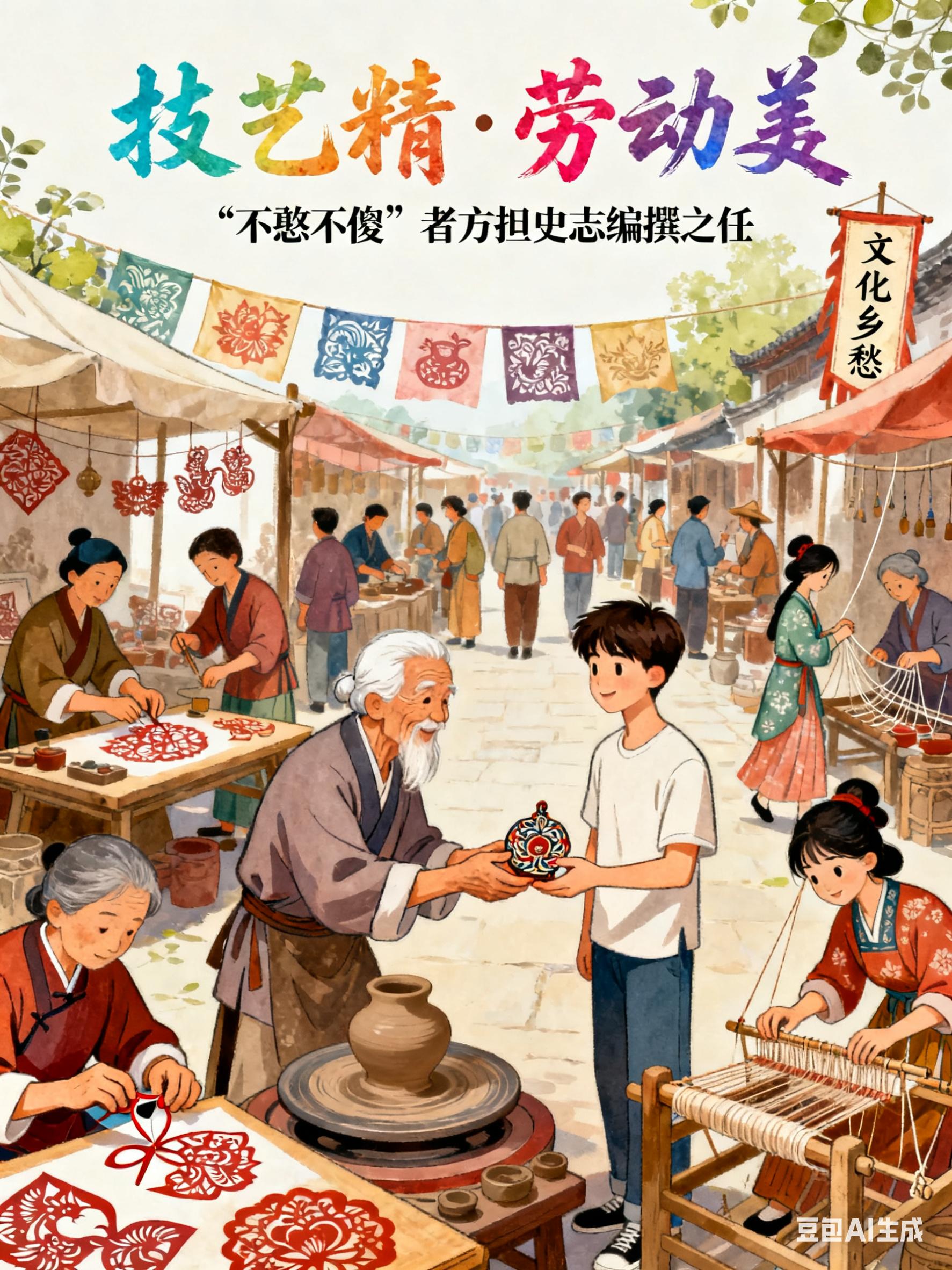
史志无言,却能映照古今;笔墨有声,足以传承千秋。史志、史话之编撰,非寻常笔墨功夫,实乃穿越岁月烟尘、打捞集体记忆、传承文明根脉的千秋大业。这份事业,既需沉潜之心,亦需通透之智,更需担当之勇,恰是“技艺精”与“劳动美”的深度交融,而能扛起这份大任者,唯有“不憨不傻”之人。
修史、纂志、写史话,归根结底是“不憨不傻”者的“静默长跑”——
他们不急不躁,不骄不媚;
他们左手“技艺”,右手“劳动”;
他们用“不憨”之勇、“不傻”之智,把散落的时光串成珠链,挂在未来民族的颈项上,熠熠生辉。
“太聪明”者,往往精于算计、敏于避祸。他们深谙人情世故,惯于权衡利弊,深知史志编撰需秉笔直书,要直面真实、不避矛盾,难免触及某些敏感话题、得罪些许利害相关者。这般“聪明人”,或怕引火烧身,不愿为一句公道话、一个真史实冒半点风险;或自视甚高,觉得伏案耕耘、埋首故纸堆耗时费力,远不及追名逐利来得快捷光鲜。他们忙于应付纷繁世事,醉心于眼前浮华,既看不上这份“吃力不讨好”的苦差事,更无心力沉下心来打磨一部传世之作,终是与史志编撰的大任擦肩而过。
“太憨太傻”者,虽或有踏实肯干之心,却难具编撰所需的通透心智与专业功底。史志、史话的编撰,绝非简单的资料堆砌、文字拼凑,而是需兼具历史眼光、逻辑思维与文字功底——要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辨真伪、筛精华,从碎片化的记忆中理脉络、找关联,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析因果、明得失。这要求编撰者既懂历史沿革,又通民俗风情;既善考证辨析,又长叙事表达。“太傻”者往往思路僵化、学识有限,难以驾驭这般复杂的系统性工作,即便有心为之,也难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佳作。
唯有“不憨不傻”者,方能集初心、能力与担当于一身,堪当此任。他们“不傻”,故而具备编撰所需的真才实学与通透智慧。他们懂历史、明事理,能以客观理性的眼光审视过往,不被片面之词误导,不被主观情绪裹挟;他们精于考证、善于梳理,能在故纸堆中披沙拣金,在口述史中去伪存真,以扎实的“技艺”将零散的史料化为系统的记载。他们“不憨”,故而拥有坚守初心的定力与直面真实的勇气。他们深知史志的生命在于真实,不因怕得罪人而曲笔讳饰,不因压力阻碍而放弃原则;他们不沉迷于短期功利,不艳羡浮华虚名,甘愿以“十年磨一剑”的耐心,在枯燥的劳动中践行“劳动美”,将心血倾注于字里行间。
史志无言,却能映照古今;笔墨有声,足以传承千秋。编撰者笔下的每一个字、每一段记载,都是对历史的敬畏,对劳动的尊重,对文明的守护。这份“技艺精”,源于日积月累的钻研;这份“劳动美”,彰显于矢志不渝的坚守。而“不憨不傻”的特质,正是这份坚守与钻研的底气——不趋炎附势、不随波逐流,以智慧辨是非,以勇气担道义,以匠心著春秋。
唯有这般“不憨不傻”之人,方能挣脱名利的羁绊、跨越能力的鸿沟,在史志编撰的道路上笃行不怠,最终留下经得起历史检验、无愧于时代与后人的传世佳作,让过往的岁月有迹可循,让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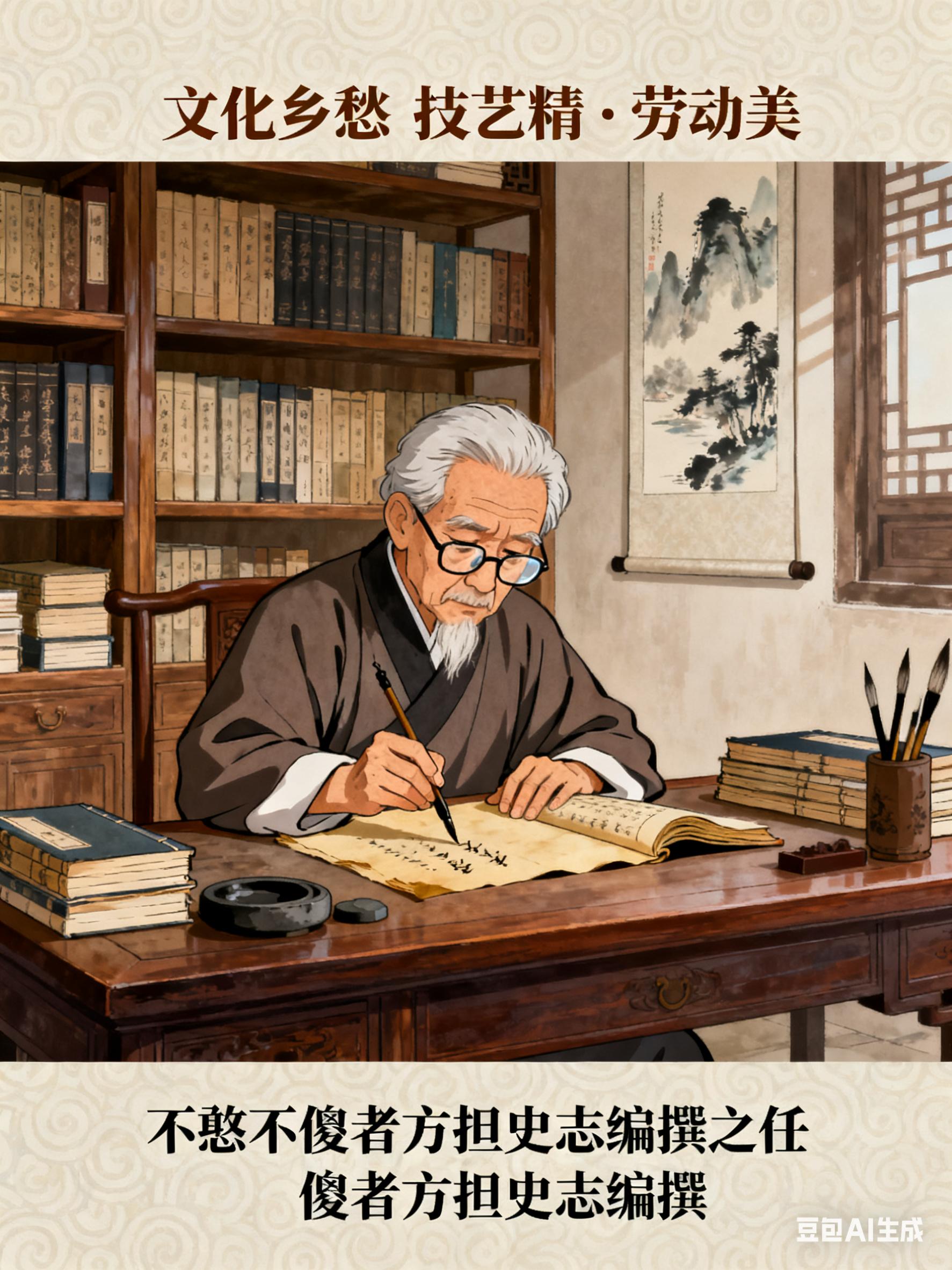
不憨不傻者,方堪秉笔立史
在历史长河的岸边,总有一群人俯身拾贝,用笔墨将散落的珍珠串成文明的项链。他们既非精明过甚的市侩,亦非愚钝无知的莽夫,而是以"不憨不傻"的智慧,在岁月长卷中留下永不褪色的墨痕。这种介于精明与愚钝之间的清醒,正是编撰"史""志""史话"者最珍贵的品质。
太聪明者常困于利害权衡。他们如精于计算的商人,在书写历史时总要先掂量笔墨的分量。明代史官王世贞曾言:"史笔如刀,刀刀见血。"当记录同僚过失可能招致报复,记载帝王丑闻恐引杀身之祸时,聪明人往往选择或曲笔隐晦,或干脆避而不书。清代《四库全书》编纂期间,纪昀等学者虽学识渊博,却因顾虑政治正确,对许多珍贵典籍进行删改,致使部分历史真相永远湮灭。这种"聪明"恰似给历史蒙上纱帐,让后人永远看不清真实的面容。
太忙者则陷于功利漩涡。他们如追逐花香的蜜蜂,总在寻找能带来即时回报的蜜源。当代社会,许多学者忙于申报课题、发表论文、争取职称,无暇静心梳理地方志脉络。某省地方志办公室曾统计,近十年间真正参与志书编纂的学者不足三成,其余多因"业务繁忙"推脱。这种"忙"恰似给历史按下快进键,让文明传承的节奏变得仓促而浮躁。
太愚钝者更难担此重任。他们如蒙眼拉磨的驴子,虽终日劳作却不知方向。民国时期,某县编修县志时,请来一位熟读经书的老儒生,但他既不懂现代史学方法,又缺乏实地考察能力,最终编纂的志书漏洞百出,成为后人笑柄。这种"愚"恰似给历史涂抹污渍,让文明传承的画卷变得斑驳不清。
唯有"不憨不傻"者,能以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完成传世之作。他们如持灯夜行的旅人,既能看到前路的险阻,又怀揣着抵达终点的信念。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《史记》,班固家族三代接力编纂《汉书》,司马光十九年如一日撰写《资治通鉴》,这些史家都具备"不憨不傻"的特质:既明白历史书写的风险,又坚守着"不虚美,不隐恶"的史德;既清楚编撰工作的艰辛,又保持着"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"的追求。
在数字时代,历史编纂更需这种"不憨不傻"的智慧。面对海量信息,编撰者要如老农选种,既要广泛收集,又要精挑细选;面对多元观点,要如匠人雕琢,既要兼收并蓄,又要去伪存真。某市档案馆近年启动"口述历史"项目,专门邀请退休教师、老工匠等"不憨不傻"的普通人参与,他们既没有学术头衔的包袱,又保持着对历史的敬畏,最终编纂的史料因其真实性和生动性,成为研究地方文化的重要文献。
"不憨不傻"的智慧,恰似历史长河中的航标灯。它提醒我们:真正的史家,既要有"为往圣继绝学"的担当,又要有"不随波逐流"的定力;既要有"板凳要坐十年冷"的毅力,又要有"文章不写半句空"的执着。唯有如此,方能在时光的淘洗中,留下经得起检验的历史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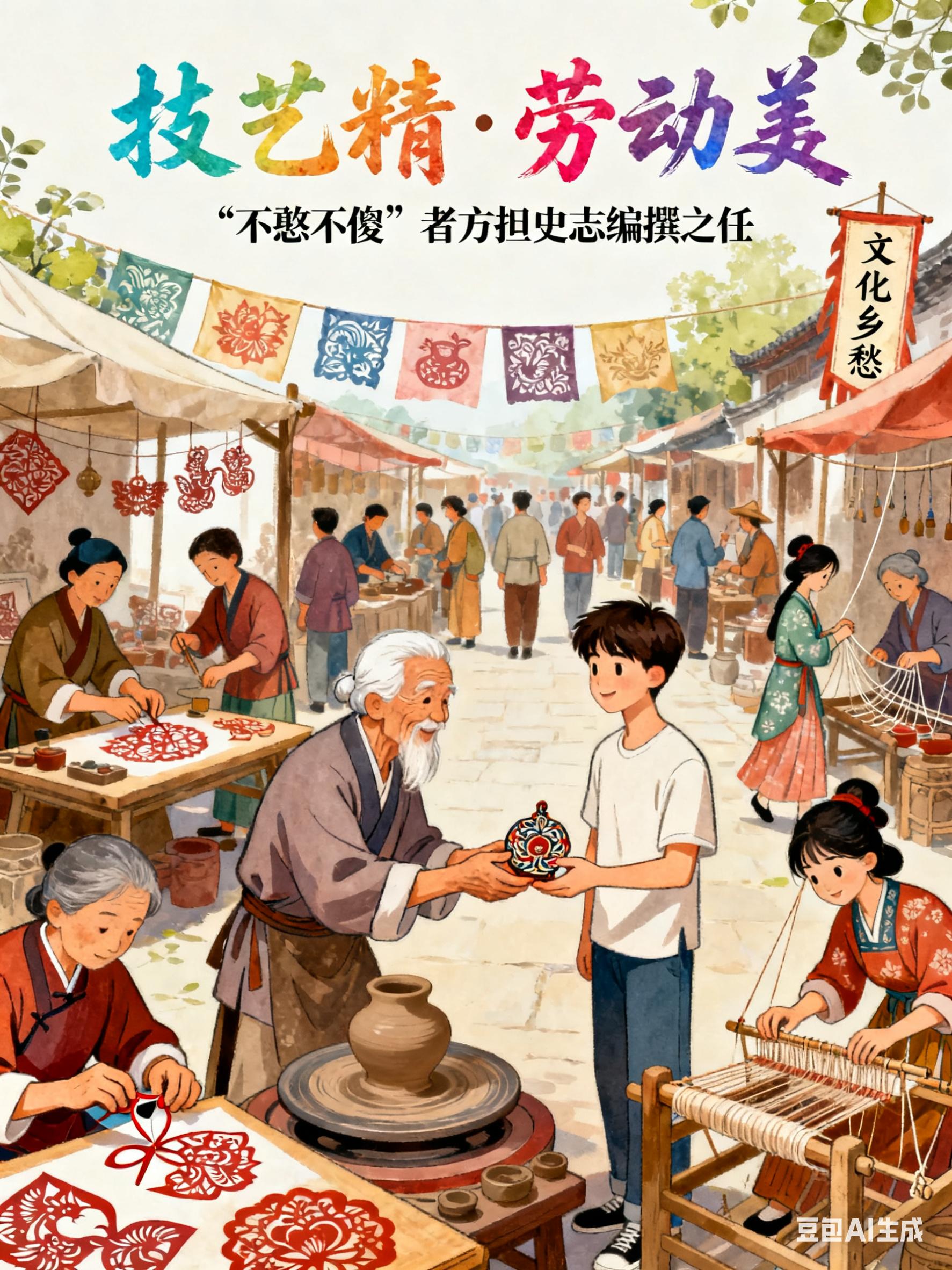
技艺精•劳动美:“不憨不傻”担起“史”“志”“史话”编撰大任
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,“史”“志”“史话”宛如璀璨的明珠,记录着一个地区、一个行业乃至一个时代的兴衰变迁,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智慧与记忆。编撰这些宝贵的文献,绝非易事,需要编撰者具备精湛的技艺与高尚的劳动精神,而能够担此大任的,往往是那些“不憨不傻”之人。
所谓“技艺精”,是编撰“史”“志”“史话”的基本要求。编撰工作需要编撰者具备扎实的历史知识、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。他们要像技艺精湛的工匠一样,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甄别,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。在这个过程中,太聪明的人往往会因为过于计较得失,怕得罪人而不敢秉笔直书,或者因为事务繁忙、心浮气躁而看不上这份需要耐心与专注的工作。他们或许有着过人的智慧,但却缺乏编撰者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而太傻的人则由于能力有限,无法理解历史资料的深层含义,也难以用准确、生动的文字将历史呈现出来。只有那些“不憨不傻”的人,既有着足够的智慧去把握历史的脉络,又有着踏实的态度去钻研每一个细节,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找到关键线索,撰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佳作。
“劳动美”则体现在编撰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上。编撰“史”“志”“史话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,需要编撰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他们可能要在枯燥的档案堆里一坐就是一整天,可能要为了一个数据的准确性而四处奔波调查,可能要在无数个夜晚挑灯夜战,反复修改文稿。这种劳动不仅仅是体力上的付出,更是脑力和心力的消耗。“不憨不傻”的人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,他们愿意为了传承历史文化、服务社会大众而默默耕耘,不图名利,不计回报。他们用自己的劳动诠释着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社会的担当,他们的劳动是美的,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。
“史”“志”“史话”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名片,是连接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桥梁。编撰这些文献,不仅是为了记录历史,更是为了让后人能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,传承优秀文化。“不憨不傻”的编撰者们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劳动精神,将历史的真相和价值传递给每一个人。他们是历史的守护者,是文化的传承者,他们的工作看似平凡,却意义非凡。
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,我们更需要重视“史”“志”“史话”的编撰工作,尊重那些为这项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“不憨不傻”之人。让我们向他们致敬,同时也希望更多有能力、有担当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,共同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因为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让历史的光芒照亮未来的道路,让人类文明在不断的传承和发展中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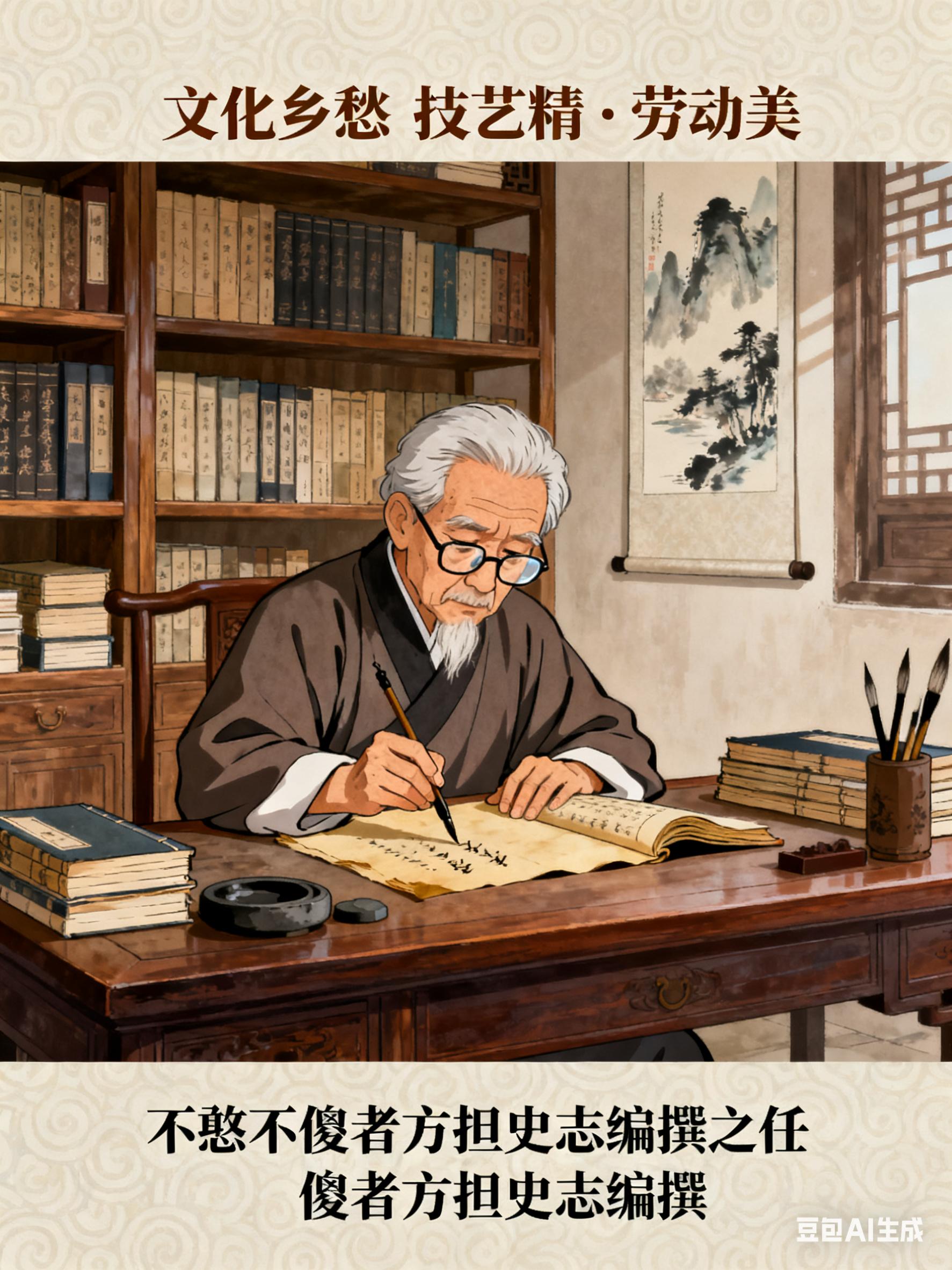
技艺精·劳动美:论“不憨不傻”者方能担纲史志编撰大任
——在智慧与执着间寻得文化传承的平衡点
一、史志编撰的本质:技艺与责任的淬炼
史志编撰非简单记录,而是对文明脉络的精密梳理。其核心要求可概括为三点:
1. 技艺精研:需贯通文献学、考古学、方志体例等专业领域。如李纪贤参与编撰《中国美术史》《中国陶瓷史》,融合文献与实物考据,展现“运用文献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”的严谨。
2. 劳动坚守:耗时耗力,需甘守寂寞。李世熊修《宁化县志》,“山居四十馀年,乡人宗之”,以毕生心血铸就方志典范。
3. 立场中立:敢于直面历史真相。刘德元指出,编史修志需平衡“存史、资治、教化”功能,既要客观记录,又要服务当代。
二、“太聪明”与“太憨傻”的双重困境
史志编撰者的选择,实为品性与能力的筛选:
- “太聪明者”之弊:
- 精于算计而避重就轻。如《颜氏家训》所讽:“一事惬当,一句清巧,神厉九霄,志凌千载”者,易陷自矜而失公正。
- 畏得罪权势,回避敏感史实。南京方言研究揭示,地方志需直面“君臣固无常分”的复杂历史关系,圆滑者难担此任。
- “太憨傻者”之限:
- 学力不足则难辨真伪。如章学诚强调修志需“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”,否则无法处理“政经典故,六曹案牍”等专业资料。
- 缺乏批判思维,易沦为资料堆砌。刘德元直言,简史编撰需“叙史与论史结合”,无洞察力者难成体系。
三、“不憨不傻”者的黄金特质:平衡的智慧
此群体兼具务实之勤与清醒之智,恰为史志良才:
1. 拙朴而专注的“匠人精神”
- 如南京方言中“拙”(意指踏实肯干者),勤勉深耕史料。田竹桥“勤勤恳恳,严谨施教”的治学态度,恰是编撰者的缩影。
- 双胞胎刺客“小晨与小夕”的故事隐喻专注之力:三年严训“合作无间”,终成顶尖——史志工作亦需此般心无旁骛。
2. 清醒而敢言的史家胆识
- 李世熊拒耿精忠伪聘,“死生有命,岂悬于要津之手”,彰显史家气节。
- 黄道周殉国前仍著《鲁迅作品论集》,其学生李世熊承其志,上书力陈时弊,不畏强权。
3. 融通古今的学术视野
- 陈平原主张“沉潜把玩”的治学态度,既需沉入史料,又需跳出框架思考。他提醒:AI时代更需警惕“检索取代阅读”,守护独立思考。
- 侯仰军著《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》,以跨学科视角“究天人之际”,得李学勤赞誉——此即“不憨”之智。
#### 四、传世佳作的诞生:以“拙匠精神”铸就文化丰碑
- 技艺与品格的共生:王瑶教导学生“沉潜把玩”,强调治学需“对世事、人性洞察体悟”,无此则难成一流学问。
- 劳动创造永恒价值:纺织史中,水转大纺车由“绳为辋”的原始工具演进为工业杰作,印证“劳动美”在技艺迭代中的核心地位。
- 时代召唤“不憨不傻”者:波兰学者斥责“大使未上任便发号施令”的傲慢,反衬史志工作者需不卑不亢,以拙守真。
结语:以“拙心”守正,以“明眸”鉴史
史志编撰如炼金,“太聪明”者流于浮华,“太憨傻”者困于浅薄。唯“不憨不傻”者:
- 以 “耿耿寸心” 坚守史笔如铁(李世熊语);
- 以 “钝学累功” 积淀学养(《颜氏家训》训);
- 终成 “陶冶性灵,从容讽谏” 之传世华章(颜之推语)。
此即“技艺精·劳动美”的至高诠释——在智慧与拙朴的平衡中,让文明薪火永续。
好的,这是一篇根据您的要求和核心观点撰写的文章。
“技艺精·劳动美”:唯有“不憨不傻”,方能担起“史”“志”“史话”编撰大任
“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。”一部真实、客观、严谨的地方志、行业史或历史话本,不仅承载着过往的烟云,更是启迪未来的明灯。编撰这样的传世之作,是一项需要极致技艺与纯粹匠心的艰苦劳动。然而,担此大任者,并非世间最聪明之人,亦非混沌愚钝之辈,而恰恰是那些“不憨不傻”的“中坚力量”。
太聪明者,往往不为也。
这里所说的“聪明”,是世俗意义上的精明。他们才思敏捷,洞察世故,深谙人情冷暖。也正因如此,他们顾虑太多。编史修志,本质上是求真,而求真则必然要触及事实,有时甚至是尖锐的、不为人喜的真相。精明的他们,怕得罪权贵,怕触碰利益网络,怕引火烧身。于是,笔锋在触及关键处时,便自觉地“绕道而行”,或语焉不详,或曲笔隐晦。一部本该锋芒毕露的史书,在他们手中,可能被磨平了棱角,沦为一部四平八稳、不得罪任何人的“功劳簿”。此外,此类聪明人多投身于能快速带来名利回报的“显学”之中,对于需要坐冷板凳、耗数载心血方能成就的编撰工作,他们从心底里“看不上”,也不愿为之付出漫长的劳动。
太憨傻者,实不能为也。
编撰史志,绝非简单的资料堆砌。它需要广博的学识、严谨的考据能力、高超的文字驾驭功夫和清晰的史学思辨。一个缺乏足够学识与智慧的人,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、互相矛盾的记载、口述不一的访谈,只会感到茫然无措。他们无力甄别真伪,无法梳理脉络,更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炼出历史的规律与精髓。其成果,或是一盘散沙,或是错误百出,甚至可能以讹传讹,贻害后人。这项技艺要求极高的精神劳动,需要一颗既专注又智慧的头脑,憨傻者确实无力承担。
唯有“不憨不傻”者,堪当此任。
何为“不憨不傻”?这是一种难得的、介于精明与愚钝之间的智慧与品格。
“不傻”,在于其能力与风骨。 他们有足够的学识和智慧去驾驭材料,有清晰的逻辑去构建框架,有精湛的文笔去生动叙述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担当。他们深知“在齐太史简,在晋董狐笔”的分量,将“秉笔直书”视为最高职业操守。为了一个确凿的日期、一个被遗忘的名字、一段被歪曲的史实,他们可以不畏艰难,遍寻蛛丝马迹。他们不怕得罪人,只怕对不起历史与后人。这份“不傻”,是技艺之精,更是风骨之美。
“不憨”,在于其执着与坚守。他们并非不懂世故,而是选择了超越世故。他们清楚地知道这项工作的清苦与寂寞,但他们更看重其无法估量的社会与文化价值。他们有一种“憨直”的劲头,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才华与生命,投入到这项默默无闻的伟大劳动中。他们耐得住寂寞,守得住书斋,将打磨文稿视为一种修行。这份看似“不聪明”的选择,恰恰源于他们对历史、对文化的最高敬意与最深沉的热爱。这份“不憨”,是劳动之姿,更是匠心之美。
正是这种“不憨不傻”的特质,使他们成为编撰事业最理想的担当者。他们以“不傻”的技艺与风骨,确保了史书的真实与深度;又以“不憨”的执着与付出,体现了劳动的价值与光辉。他们的劳动,是智力与体力、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,是将冰冷史料转化为鲜活历史的艺术创造。
因此,当我们赞美一部传世的史志佳作时,我们不仅要看到字里行间闪烁的“技艺精”之光,更要感受到背后那位“不憨不傻”的编撰者所付出的“劳动美”。是他们,以非凡的勇气、智慧和坚守,抵挡了时间的侵蚀,为我们,也为未来,留下了最宝贵的记忆与最清醒的镜子。这,正是“技艺精·劳动美”在历史长河中最深刻、最动人的诠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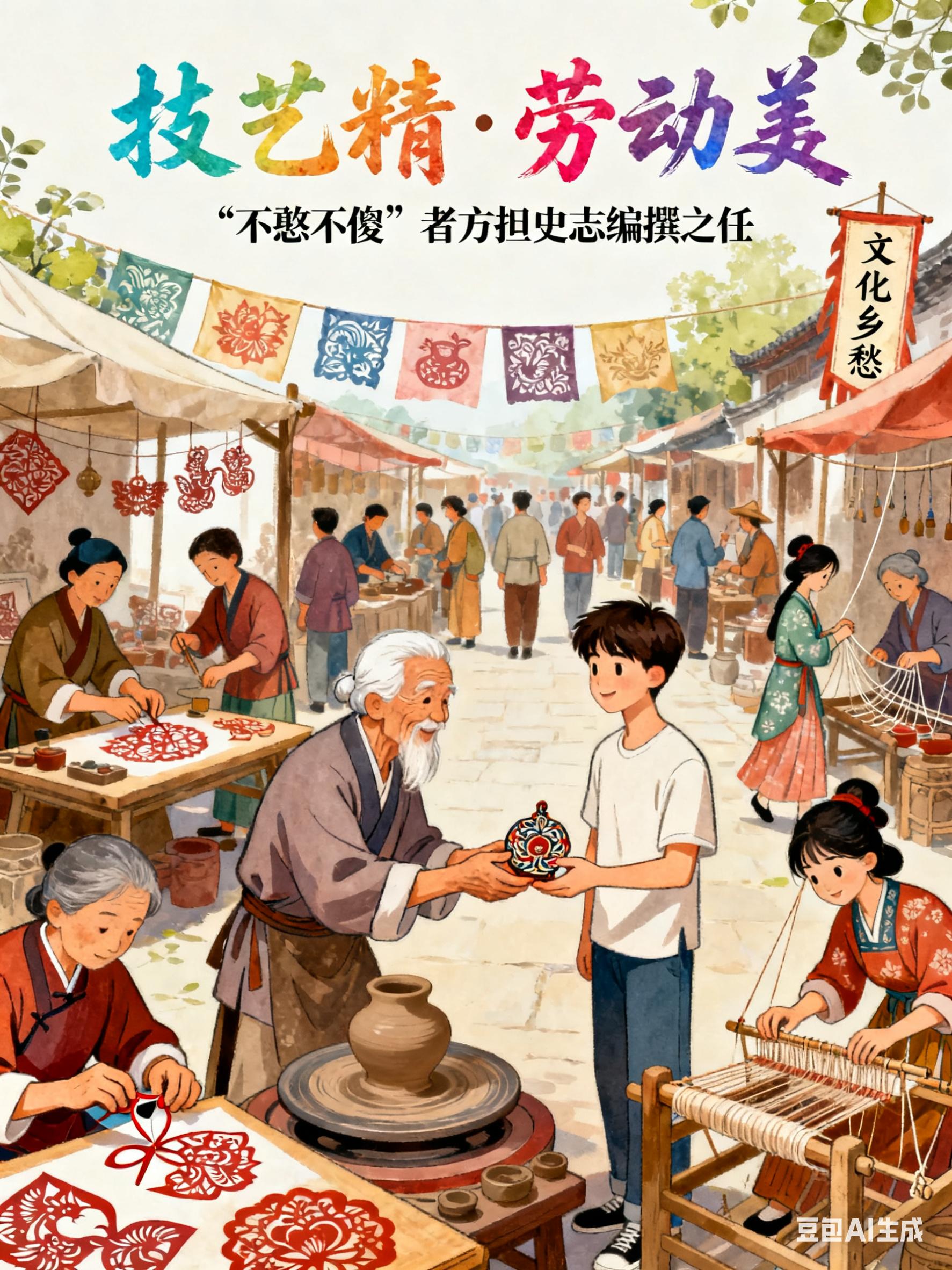
技艺精·劳动美:唯有“不憨不傻”者,方堪“史”“志”“史话”之任一、引子:三副面孔,一种宿命
每逢盛世,官方、民间、家族便不约而同动起“修史”“纂志”“写史话”的念头。于是,书案上很快出现三种人:
1. 太聪明者——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,一句“得罪人的话”不肯落笔,结果满纸“圆融”,读来如嚼蜡;
2. 太傻者——热情可嘉,却分不清“嘉靖”与“嘉庆”,把“知府”写成“知县”,把“第二次”写成“第三次”,稿成即废;
3. 不憨不傻者——看似“中庸”,实则“中坚”:既敢“顶真”,又能“顶硬”;既懂“考据”,又肯“跑腿”;既识“分寸”,又敢“下笔”。
历史最终记住的,总是第三种人。
二、“不憨”:不憨不是愚忠,而是“敢”1. 敢“得罪”——
清人章学诚修《湖北通志》,把当地巡抚祖上“占田三千顷”照实写下,幕僚夜叩门求删,章答:“志者,千古之公器,非一人之私谱!”声震屋瓦。
2. 敢“笨”——
顾炎武写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徒步十九省,边问边抄,手稿重达八百余斤。有人笑他“憨”,他却说:“考据之业,九分跑腿,一分读书。”
3. 敢“磨”——
苏州博物馆藏《苏州工志》稿本,平均每页改八遍,蝇头小字密密麻麻。主笔王佩诤自嘲:“我这不是写文章,是在‘磨’文章;磨到对方没脾气,也就对历史有交代了。”
三、“不傻”:不傻不是油滑,而是“会”1. 会“入档”——
今日修志,首在档案。上海二轮修《黄浦区志》时,编委周蕙带组员把区档案馆一百多万张卡片逐条过筛,最终补回“失踪”的48家上世纪50年代合营企业,补档案3.2万卷。
2. 会“跑路”——
编《义乌市志》“小商品市场”章,副主编楼益圣三赴廿三里,把1982年“马路市场”第一天的摊位分布画成“复原图”,图中每块砖头都对应口述与航拍,被商务部档案处一次收藏。
3. 会“用数”——
《中国工匠史料辑录》团队用Python爬梳《清实录》3200万字,抓取“匠”“作”“营造”关键词,再人工复核,三年得11万条有效记录,一举把“工匠”从边缘词变成“数字人文”热词。
4. 会“讲故事”——
《北京三岔河村史话》作者刘一达,把“村口一棵老槐树”写成“全村人的计时器、公告栏、婚姻介绍所”,一句话让年轻人转发十万加。史话不是“史料压缩包”,而是“情感路由器”。
四、“技艺精”:手艺不到,一切白搭
1. 编年体、纪传体、章节体,各有一把“钥匙”;
2. 标点、校勘、注释、索引,四项基本功缺一则漏;
3. 舆图、遥感、GIS、无人机,新工具不会用便落后;
4. 纸质、电子、音频、视频,多模态发布是标配。
一句话:既要“老派功夫”,又要“新派技术”,缺一门都称不上“技艺精”。
五、“劳动美”:一撇一捺都是“脚力、眼力、笔力”
1. 脚力——
《云南省志·茶马古道卷》为确认一段50公里古道,编委夏天徒步12天,海拔爬升4600米,回来每人掉了8斤肉,却换回明代摩崖题刻13方。
2. 眼力——
《温州手工业志》主编陈明楷在旧纸厂垃圾堆翻到一册1934年“瓯绸染色配方”,抢救回“已经失传”的27种植物染料,让“瓯绸”得以复活。
3. 笔力——
《敦煌石窟志》一句话描述壁画病害:“疱、鼓、龟裂、起甲、粉化、烟熏、划痕、盐霜”,8个名词、8种图像、8套治理方案,一个字也不能错。
“劳动美”不是口号,是“汗味、土味、纸味”混合的“三味真火”。
六、收笔:给后来人的三句“不憨不傻”箴言
1. 对历史——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,少一分也别多一句。”
2. 对当事人——“笔下有人,纸上才有魂;眼里有光,字里才有温度。”
3. 对自己——“把名字写在书的最后一页,而不是第一页;让书自己开口,别替它抢镜。”
修史、纂志、写史话,归根结底是“不憨不傻”者的“静默长跑”——
他们不急不躁,不骄不媚;
他们左手“技艺”,右手“劳动”;
他们用“不憨”之勇、“不傻”之智,把散落的时光串成珠链,挂在未来民族的颈项上,熠熠生辉。